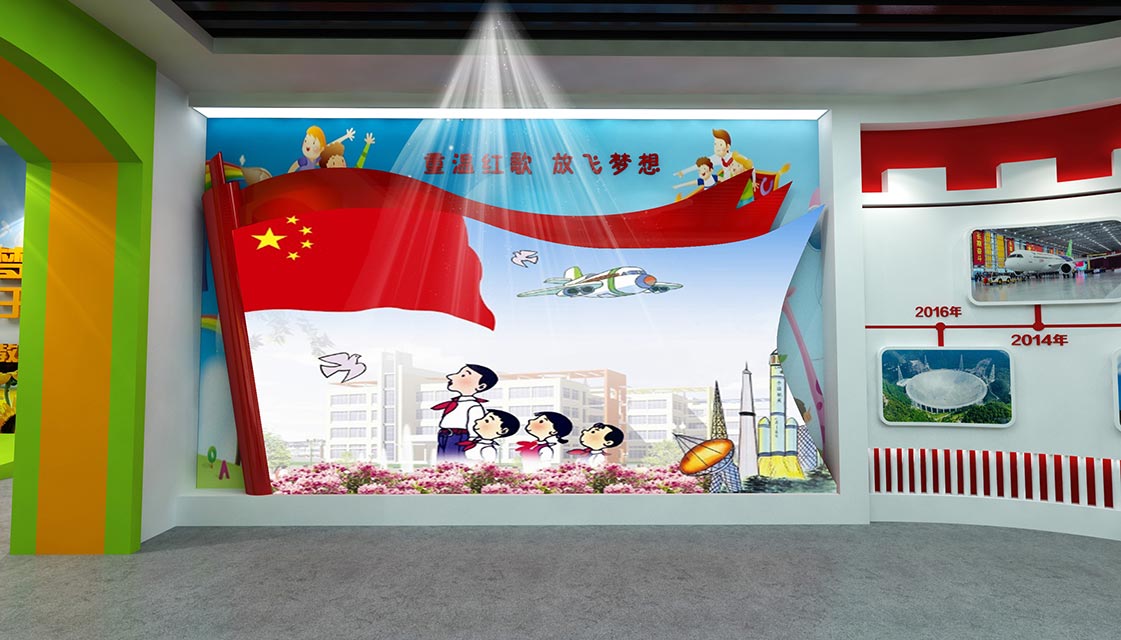日本东京某私立医院内,工作人员正在给病人登记。
本报记者 刘军国摄

2017年7月,11名西班牙“洋中医”来到位于昆明市的云南省中医院学习推拿和针灸。图为中国老师指导“洋中医”。
人民视觉

民众在德国体验背负式康复机器。
本报记者 管克江摄

澳大利亚华裔医生刘英在为患者检查身体。
本报记者 李 锋摄

意大利罗马一家大型综合医院,这里频繁有救护车抵达运送病人。图为其中一辆刚刚运送病人抵达急诊室的急救车。
本报记者 韩 硕摄

提起看病,不少人会羡慕发达国家的一些医疗福利,其实发达国家医院里的久待候诊、昂贵费用、误诊事故等情形也屡见不鲜。医疗福利“看上去很美”,享受起来却并不容易,本报驻外记者在此跟大家分享他们在发达国家看病的体会
看病离不开“等、等、等”
不久前,一则德国37岁孕妇流产的新闻令人痛心。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小镇上,一名怀孕3个月的孕妇因突然腹痛被丈夫送往附近医院急诊。然而,由于只有一名急诊医生,前台护士又认为孕妇无大碍,在经过长达4小时的漫长等待后,孕妇因为大出血才被紧急推进手术室,此时胎儿早已死亡。德国看病“治病不救急”的特点可见一斑。
类似事情,本报驻德国记者也领教过。一次凌晨1点,记者突发急性肠胃炎,疼得满头冷汗,打车去附近一家医院急诊,发现急诊室里人满为患。前台护士简单问询后,便开启了等待模式。在熬过一小时后,一名建筑工人模样的男子终于被医生叫号。“在手指骨折4小时后,我终于要见到医生了!祝福我还能拥有完整的手指吧!”男子高举简单包扎、渗着血迹的手指,向所有人鞠了一躬,戏谑的语气里充满愤怒与无奈。听完男子的发言,记者放弃了等待,好在临走前护士给了几包能缓解症状的药物,熬过了那晚。此后,记者一般情况下再不去看急诊。
根据德国相关法律,每位拥有行医执照的医生都有义务定期参与急诊服务。然而,这一义务一般只在工作合同中提及,联邦层面并没有统一规定医生参与急诊服务的最低频率和时间。结果,德国现有急诊医生力量远远不能满足病患的需求,名为“急诊”,病人却急不得,只得漫长等待。
在梅克伦堡—前波莫瑞州,当地政府为鼓励医生多值急诊班,甚至补贴每小时18欧元的值班费。德国联邦消费者中心协会专家福格尔指出,这依旧不能解决德国医疗最本质的问题,就是医生资源过少。
在加拿大,有一年4月份,本报驻加拿大记者的牙齿出了点小毛病,给一家牙医诊所打电话,对方的回答让人吃惊不小:“我们已经预约到7月中旬了,可以给你安排在7月下旬。”记者连忙询问,有无可能提前一些,毕竟3个月的等待太长。对方答,如有人取消预约就安排。后来确实有人取消了,但记者也无法继续等待,只得提前去药店拿了些药缓解症状。与朋友聊到在加拿大看病难,这位朋友建议道,如果你有慢性病,需要处方药,而又没有家庭医生,最好找医生朋友一次开个两年的,省得以后看医生麻烦。
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今年1月底公布了最新的政府医疗服务报告,披露了诸多让人触目惊心的医疗事故。报告指出,给不该做手术的病人做手术,手术部位错误、手术器械留在病人体内、输错血液等,都是澳大利亚医院里常见的医疗事故。虽然欧美等国家建立了完备的医疗体系,但医院效率、普通医生和护士的水平却远远跟不上现代医学的发展步伐,加之高福利制度监管不严等,导致这些国家医疗事故高发。
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对美国、加拿大和英国等7个发达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,每300名住院病人中就有一人死于医疗事故。失误除了使用复杂药物的原因外,还包括医疗人员劳累过度、人手不足、沟通不畅等。
另一份来自法国参议院的报告也指出,法国每年有1.8万人死于治疗方法不当、剂量不当、后续监测不力等原因。在澳大利亚,每年有1.8万人因医疗疏忽死在医院;每年有5万人因医疗疏忽遭受永久性伤害;每年有8万人因医护人员用药错误不得不住院治疗。
去年年初,法国布雷斯特市一家医疗中心因2009年一起人工流产中的子宫肌意外穿孔事故,被判处总额超过54万欧元的罚款。据法国国家医疗事故赔偿机构主席勒鲁介绍,2016年该机构共收到4500多项赔偿要求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医疗事故的数量之众。
德国患者安全联盟的医疗事故数据更为惊人,光是医生把手术纱布或棉球遗落病患体内的事故,每年就有约3000起。德国医生协会的统计显示,每名德国人平均每年需就诊19次。德国人口约为8000万,与37万名现职医生相比,后者的工作强度不小。近年来,德国政府频频向外国医生伸出橄榄枝,然而,外国医生因语言不通交流不畅,加之高强度的工作,也增加了就诊失误几率。
此外,高福利制度监管执行不严,养出蠹虫。以法国为例,2018年年初两名前医护人员因从医疗保险中欺诈获利63万欧元(约合人民币492万元)被地方法院判刑,其中一人在2010年到2014年间利用助产士的便利,采用虚报发票金额、开具假发票、滥计出诊费等方式,从疾病保险金库获利27.7万欧元;另一人作为自由执业的护士,在一年间开立了1.8万份医疗票据,是正常水平的3倍之多。
不可否认,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有其优点。以加拿大为例,加拿大居民不论居住在什么地方都有健康卡,凭卡看病,绝大多数的医疗服务都是免费的。但正如一个硬币有两面,渥太华医学院教授雅格·布莱文津指出,因为看病免费,人们即使没有严重或紧急病情,也会预约医生进行检查,导致候诊名单很长,并且造成医疗资源浪费。同时,政府为医生规定了接诊人数上限。此举本意是为保障医生权益、保证医疗水平、控制支出,但无疑进一步延长了患者的等待时间。布莱文津表示,加拿大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够优化。外国人如果无法进入加拿大的医疗体系,不仅享受不到免费医疗,而且看病会更难更贵,因为找不到家庭医生,多数情况下只能去医院看急诊。
在澳大利亚看病也是免费的。但患者在公立医院没有权利选择医生,也不能选择何时住院或者手术。澳大利亚华裔医生刘英在堪培拉从业已经近28年。她认为,澳公立医院效率低下情况比较严重。“如果一名医生在私立医院每小时可以做4个肠镜检查,那在公立医院每小时最多只能做2个。由于效率低,病人等待手术的时间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一两年。”
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,一方面是致力于发展全民医保,另一方面是社保体系下的严重赤字和公立医院的不堪重负,为医疗系统增添重重危机。以法国为例,由于国家财政捉襟见肘,医疗保健预算一再被压缩,公立医院医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。工资不高、工时超长,直接导致医生大量流失。如何在减少开支的情况下更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,确保民众和医护人员双向满足,将是发达国家医疗模式不得不应对的问题。